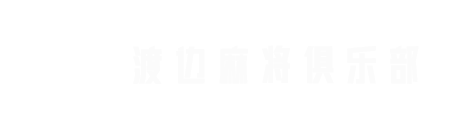“您是说那药还是没用?”尼尔森·朗曼医生扶了扶眼镜,向坐在对面的人确认道。
这是一位英俊的黑发男性——年龄在四十岁上下,穿着讲究——此时正抚着眉间叹气,“不能这么说,它的确能让我一觉睡到天亮,但是相应地,噩梦也更长了。”
“您提过许多次。”朗曼医生一边说,一边起身走向墙边的资料柜,“威廉·肯特,威廉——噢,找到了,我看看……第一次是在二月,然后是四月,越来越频繁……您还记得噩梦的内容吗?”
肯特点点头,又摇摇头,“我记不清了。”
症状加重。暴躁易怒。噩梦频繁。朗曼拿起笔写下几个词,皱着眉思索了片刻才开口。
“听我一句,伯爵,您还是该回庄园去住。不管怎么说,有人照顾着总是好些。”他劝告一般说道,“这么多天过去,夫人应该消气了……她还是关心您的。”
“我了解路易莎,她可不会那么轻易原谅我。”肯特伯爵答道,“不过你说得对,我是打算回去——今天是乔治安娜的生日。”
“乔治安娜小姐!那她见到您一定很高兴。”朗曼医生笑着说,“她该有十三岁了吧?可惜我这儿没准备什么礼物……”
肯特伯爵摆了摆手,又指了指门边的一个皮箱,“我给她订做了一把小提琴。本来想买匹小马送她,但没看到合适的——那孩子成天就知道看书,我可不希望她变成个书呆子。”
“那还不是学您的?”朗曼医生打趣道,“过去夫人可没少说您是书呆子来着。”
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,肯特伯爵心情好了不少,起身告辞。
“我还有事。”他对送自己到门口的朗曼医生说道,“你快进去吧——我听到小茱莉亚在喊爸爸了。”
马车在树林外停下。肯特伯爵从车上跳下来。
“不用在这里等我了。先回庄园,告诉夫人和小姐我很快就到。”他对车夫说,“记得将那把小提琴交给小姐——噢,不了,还是我亲自给她吧。”
他伸手从车里拿下琴箱,拎在手里。车夫显然不太放心,“可您一会儿怎么回去?”
“我会去借匹马。”
马车离开了。肯特伯爵在原地站了一小会儿,转身走进树林。
深冬的冷风从北边灌过来,将树叶打出嘈杂的沙沙声。虽说正午刚过,但天空被灰沉沉的云覆满,丝毫透不出阳光的暖意。肯特伯爵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,脚步不由得加快了些。
这几天的争论毫无成果。年轻的子爵毫无疑问已经走火入魔了,那两位教授也是。没有一个人愿意好好听自己说话。他们只一味地期待着那所谓真神的降临,而阿尔瓦·克拉克在听说他把法术书毁了后更是又惊又怒。
“只是因为路易莎反对,你就不敢继续了?”他气急败坏地指着肯特伯爵叫道,“一年!我们研究了足足一年!而你现在说要放弃?不可能,听着,威廉,我绝对不会把抄本给你,如果你想中途退出,把笔记交出来,那我们可以不计较你的背叛……”
最终当然是不欢而散。肯特伯爵思来想去,放弃了再次去说服朋友们的想法,打算趁克拉克不在家的时候——他最近几日都在城里,来不及拿走它——去把抄本偷出来。
路易莎说得没错。那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甚至敢肯定,自己的噩梦、精神状态不稳定就是研究那些东西造成的。只要毁掉阿尔瓦手上的那一份抄本,那么他们就无法继续研究。接下来再把花园里的法阵破坏——
“伯爵?伯爵?”
肯特伯爵从沉思中回过神来。他发觉自己已经走到了克拉克的别墅外,老警卫正从窗口探出头向他打招呼。
“啊,老约翰。”他定了定神,露出微笑,“阿尔瓦在家吗?”
“子爵说是要去天文台查什么资料,这几天都没回家。”警卫回答,走出来给他开门,“您怎么突然来了?要我们通知子爵吗?”
“不用了。”肯特伯爵连忙说道,他走进院子,“我过来找一本书——之前忘在这儿的,应该在书房里。”
警卫点点头,也没有再多问,叫来女仆,“快带伯爵去书房。”
克拉克的藏书不算太多。在四人之中,他算是最不爱钻研学问的一个了,但性子又最激进,总是想尝试“新鲜的东西”——肯特伯爵拒绝了女仆送上来的茶点,关上门急急忙忙翻找起来。
书柜里——没有。书桌上——没有。他甚至将卧室也找了一遍,没有任何收获。阿尔瓦无意中提到过,抄本就放在书房,除非他没有说实话……
也许是藏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了吧。
肯特伯爵坐在书桌旁思索着,目光落在了书柜的边缘。他站起身,正打算重新翻找一次,楼下却传来了整点的钟声。
乔治安娜应该在等爸爸回家吧。好几天没见到她了,想必她有很多话想说。路易莎不知道消气了没有,也许得先告诉她自己已经退出研究了,不然她一定还会担心……
肯特伯爵在原地迟疑了一会,最终还是转身走出了书房。克拉克在找到星象图对应的日子之前应该都不会返回别墅,自己明天还可以再来一趟。
他向别墅的管家借了匹马,匆忙地离开了。
切斯特庄园在西南边,离这儿六七英里。跑快一些的话,还赶得及在下午茶之前到达。
天空越来越暗,风声呼啸,没多久便下起了大雨。肯特伯爵伸手将帽檐往下拉了拉,试图遮挡朝自己袭来的雨滴,又用左臂环住了身前的琴箱,只留一只手抓住缰绳。
他心情急切,便没有沿着平时的路,想从林子间直穿过去。雨水浸透了地面,马儿似乎不乐意再继续走了,时不时地放慢步子。肯特伯爵不耐烦地踢了踢马肚。
那种暴躁的情绪又来了。他记得很清楚,每次出现这样的情绪时,他都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一举一动。带着没来由的愤怒,他又狠狠地踢了一脚。
马儿吃痛向前狂奔起来,在树木间一深一浅地颠簸着。他无法继续保持平衡,手臂一松,琴箱便从怀中掉了出去。
肯特伯爵先是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,发现那箱子在草地上摔了开来,棕色的小提琴跌了一下后横在了地上,迅速被雨打湿。
他当然立刻想到要去捡起来,但手脚却仿佛不听使唤地进行着违背大脑的动作。
回去——他用力驱赶着马儿——停下——他左右拉扯着缰绳——回去——他疯狂踢打着马肚——那是乔治安娜的生日礼物——
那是乔治安娜的生日礼物。
他从马背上跌落,后脑勺重重地撞上了一块石头。去找回来,他还想着,但身体完全无法动弹。马儿已经跑远了。这儿离庄园没多远,就在这儿等人过来吧。真是糟糕,看来赶不上下午茶了。噢,糟了,摔下来的时候帽子似乎掉在了地上,那还是路易莎前不久买回来送给他的,如果她看到自己这么不爱惜它,恐怕又要生气了……
抱歉,路易莎。抱歉,乔治安娜。
威廉·肯特伯爵面朝上躺在草丛中,睁大眼睛望向天空,他最后看到的情景,是雨滴从树叶的缝隙中落下来,接连不断地打在自己身上。